人间四月:试寻野菜炊香饭
韩建慧/文 齐艳芳/图
2023年05月26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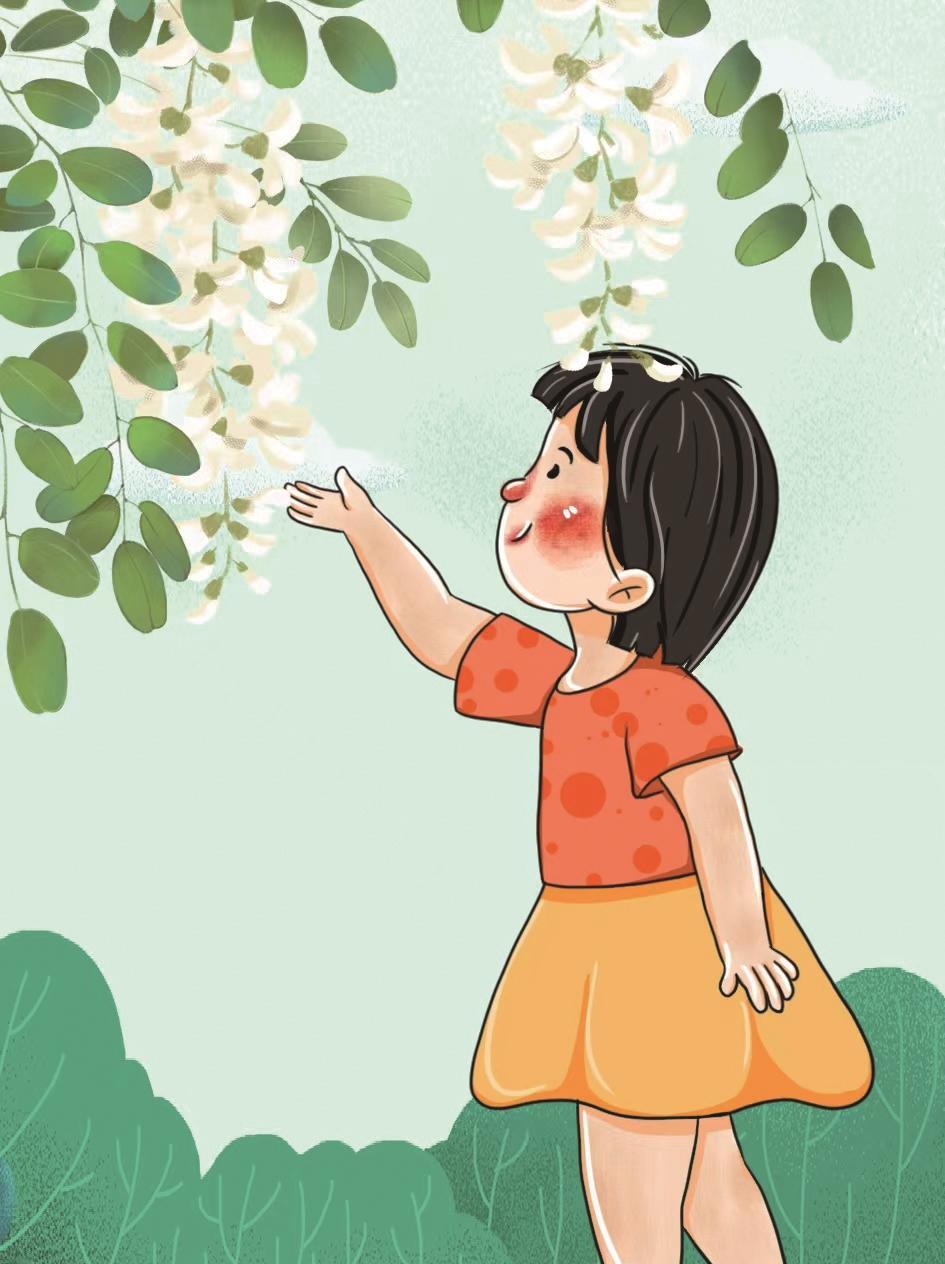


■黄河岸边是我家·寻味乌海 ⑴
开栏语
每一座城市,都有自己的风韵和味道。
都说美食是开启城市烟火气的灵魂。春夏秋冬,晨昏轮转,一重滋味就是一段生活。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,无边岁月里的炉火明灭,漫漫时光中的炊烟袅袅,最终都化作平凡的三餐四季。
都说美食是追回童年记忆的味觉密码。灶火燃起,香气弥漫,妈妈的手艺早就植入记忆深处,再平凡的食材也能成就未来几年、几十年的惦记。万户千家,味道迥异,但幸福的滋味却何其相似。
都说美食能承载游子思乡的行吟。三餐一宿,岁短日长,故乡是我们抵达世界深处的一个起点,美食是我们回望故乡时最柔软的情愫。家乡味与家乡话一起,愉悦了味蕾,抚慰了身心,风尘恋恋中定格成关于家族人事、故乡山水的特殊记忆。
乌海是一座移民城市。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族群众,用他们的智慧和对生活的热爱,在传承和交融中,创造出的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的饮食文化,经岁月打磨,成为乌海人特别热爱的一重风味。
这重风味与辽阔的蓝天白云有关,与苍莽的金沙戈壁有关,与潋滟的一湖碧水有关,与壮美的山海沙城有关……它不仅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,还在无形中承担起了促进人类情感、凝聚社会群体的作用。
如果您也想寻访这重“乌海风味”,领略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普通人的极致情感,不妨跟随记者一起,开启这段“寻味之旅”。
小满刚过,芒种未到,正是农历四月风光最盛时。
农历四月,最盛的不只是“始盛开”的山寺桃花,还有各种野生野长的野菜。
说起野菜,许多人都有格外绵长的回忆。野菜不独是“菜”,地里生的、树上长的、水畔飘的,但凡无毒且能入口的植物,都是老百姓嘴里的“野菜”。忆往昔岁月,野菜是人们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填饱肚子的代食;到如今物质极大丰富,野菜又是人们忆苦思甜时寄托情感的首选。
北方的春季短暂,但野菜的品种却不少,苦菜、沙葱、马齿苋、榆钱、槐花、蒲公英……几乎所有叫得上名儿的野菜,都藏着人们难忘的回忆。
苦 菜
一场小雨过后,道边的绿化带里,苦菜悄悄连成了片。
68岁的孙福荣带着塑料袋和小铁铲,不一会儿就铲了一袋。鲜嫩的苦菜苗带着清晨的露水,跟他记忆中母亲带他挖的一模一样。
20世纪60年代末,孙福荣的家在铁路沿线李华中滩养路工区,五口之家只靠着父亲一人每月60多元的工资生活。当时每人每月的供应粮是13.5公斤,爷爷和奶奶还在世,父亲的工资每月要固定拿出5元寄回老家,因此家里的粮总是不够吃。
孙福荣的母亲在附近的工区帮工,闲暇时就会带着他和弟弟,母子三人去山沟里、小河边挖苦菜。那是一种灰绿色的叶片,紧紧地贴着地面舒展,到了季节还会绽放出一朵朵淡黄、青白或是淡紫色的小花。
苦菜洗干净,被母亲在开水锅里焯过,稍稍搁一点醋和豆瓣酱用来调味。几个孩子围在母亲身边,最期待的就是看她从橱柜深处拿出一个塞着输液瓶橡皮塞的小瓶来,里面装的是香油。母亲珍惜地往碗里滴上一滴,笑着说,想要凉拌苦菜好吃,一定得滴个“油花花”。这滴“油花花”的味道,60年来一直萦绕在孙福荣的鼻尖,从未散去。
与孙福荣一样,今年53岁的陈美河也对苦菜情有独钟。小时候她生活在拉僧庙镇,一到春末夏初,田野里、山坡上、地垄处,零零星星的苦菜就钻出来了。
苦菜的生命力极为顽强,无论自然条件如何残酷都照样生长。春天干旱少雨,土地都干涸龟裂了,苦菜仍能在裂隙处探出头。小孩子徒手拔苦菜是拔不动的,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入地里,快有半尺深。长老了的苦菜有奶白色的汁水,凉拌吃不得,便用它来熬粥,或者剁碎掺在棒子面里贴苦菜饼子。
“那时候的孩子,还没有尝到生活的甜,就先尝到了苦菜的苦。”陈美河说。
“春风吹,苦菜长,荒滩野地是粮仓。”一句民谚道尽了人们对苦菜的特别情愫。
时至如今,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,苦菜不再是人们的续命粮,反而成了健康美味的代名词。
经营着一家蔬果超市的张贺告诉记者,目前市面上在售的野生苦菜每公斤14元仍供不应求,便是种植的苦菜,每公斤也能卖到7元左右。
为什么以前的“续命粮”,而今成了抢手货?孙福荣颇为感慨:“除了苦菜的确具备明目、泻火等保健功效外,也许是它能勾起人们忆苦思甜的情结吧。”
沙 葱
沙葱,西北地区人们独享的大自然的馈赠。
凉拌沙葱和凉拌苦菜一样,从来都是百姓餐桌上常见的美味。这种耐寒耐旱的野菜,春季生长,全年可食,做法丰富,口感亦佳。
曾几何时,沙葱也是戈壁地区人们春季难见绿色蔬菜时最好的选择。
今年82岁的苏映山还记得自己刚从山西到乌海时靠沙葱当菜的故事。
1961年,苏映山听说乌达煤矿在招工,就不惜千里拖家带口地来了乌达。
彼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,农村日子过得也很艰难,当工人总有口饭吃。然而到了地方他才发现,这茫茫的戈壁滩上,吃和住都是问题。苏映山住在了前辈腾给他的一个地窨子里。矿区当时管饭,甚至可以带家属一起来吃。第一顿饭,他和妻子一人领到一个半尺长的馒头,然后,一盆盐渍的沙葱摆到了桌子中央。
“叫我来的老乡招呼我说,快吃,这可是好饭啊!我饿得前心贴后背,夹了一筷子沙葱夹在馒头里,咬一口下去,觉得又辣又香。”他说。
工休的时候,拔沙葱就成了矿工们的乐趣。那沙葱长在石头缝里,长在半山坡上,长在低水洼边,有水的地方长得青葱茁壮,没水就细如韧草,却不影响其美味。拔回来的沙葱,茎嫩不易久储,便洗净汆烫,拌上大粒盐和醋腌起来,足足能吃半年。
生活好了以后,沙葱便也是口粮菜,吃面条的时候用沙葱炝锅,面条汤里就带出了丝丝葱香味儿。用新鲜沙葱蒸玉米面包成的沙葱团子,能放好久当干粮,若是赶上有羊肉,也要把羊肉和沙葱一块剁碎了包包子、包烧卖,那就是无上的美味。
如今,沙葱更是成了百姓致富的好路子。
海南区巴音陶亥镇就有这样一个沙葱产业生态园。沙葱播种一次,可连续采收15年,一年能收割六七茬,一茬能收500公斤左右,销往呼和浩特、包头、银川等地,俨然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。
槐 花
时下又到了槐花飘香的季节。
我市很多街路都种植有槐树。槐花盛开的时候,满街飘香,关于槐花的迷人回忆也就随之而来。
市民孙臻说,她每天路过人民广场附近闻到槐花香时,都忍不住流口水,想念奶奶包的清香可口的槐花馅包子和饺子。可惜道边树过于高大,带个梯子采槐花也很不文明,纠结了几天后终于想起了万能的互联网,一搜索果然有卖干槐花的,兴奋地下了一单。当她提着槐花去奶奶家时,一进门老太太就喜出望外地喊道:“这是哪里来的槐花啊,可真是稀罕物儿!”
如今的“稀罕物儿”在孙臻的童年并不稀罕。那时候,他们一家9口人住在乌达砖瓦厂附近,院子里就有两株大槐树。“每年农历四月都是槐花盛开的时候,爸爸和小姑背着麻袋爬到树上,一会儿就摘一麻袋。妈妈和奶奶用大盆子将槐花淘洗干净平铺晾晒,预备出包包子、包饺子的馅来。那洁白的、晶莹的小花苞,总是吸引着我和妹妹悄悄伸出小脏手,偷几朵笼在手心里,嗅一下,沁人心脾。”
无独有偶,市民肖萍也对槐花怀着一份甜蜜的记忆。她和丈夫的初见就是在家门口的槐花树下。也是初夏时节,也是一个风清日暖的天气,母亲拉着水管浇树,她站在槐树下眼巴巴地看树上的槐花,胖嘟嘟的弟弟胆小,爬到一半就不敢上了,姐弟两个缠着母亲要找园艺剪子来剪树上的枝条。
邻居家门口站着看热闹的老夫妻,听到她要剪枝急忙阻拦:“哪用得到找树剪子,我侄儿中午来吃饭,让他给你摘点。”话音未落,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背着一捆电缆从小路尽头拐进来,黝黑的面庞,笑起来牙齿如槐花一般白。
肖萍说,那天,这个叫冯陆军的男人帮她摘了很多槐花。母亲施展手艺,蒸了“傀儡”,烙了槐花饼,炒了槐花鸡蛋。两家人围在一起享用槐花的清香,也在一对青年心中种下了甜蜜的种子。
榆 钱
“谁没吃过榆钱饭呢。”
说起榆钱,81岁的高秀敏说:“那可是老百姓填肚子的天赐粮呀!”她的女儿,64岁的毛爱花则笑:“那还是咱们小时候解馋的好东西哩。”
作为多风少雨的西北内陆城市,乌海地区多榆柳,榆树见水就能活,曾是人们用来防风固沙、美化家园最常见的树木。
每年春来时,冬天掉光了叶子的榆树就开始发芽开花,清明前后便成熟结果,一串一串挂在枝头,圆而小,仿佛一枚枚小小的铜钱。榆钱的果实期很短,如果不刮风,也就是一周左右,刮风的话,三四天就飘零满地。想吃榆钱饭,一定要在果实最为鲜嫩的时候将它采摘下来。
毛爱花记得,从记事起,每年她都会被兄长们带着爬树去“唰榆钱”,一串一串的榆钱被从树上“唰”下来,放在布袋子里揣洗,直到洗得嫩绿嫩绿。新鲜的榆钱就算不做加工也能吃。几乎没有什么零嘴儿的小孩们一把一把地将榆钱塞进嘴里,嚼一嚼,满口都是淡淡的青草香气。
老榆树浑身是宝,榆钱吃罢了还能吃榆叶,嫩榆叶一样能在关键时候当代食。高秀敏说,在那些青黄不接的日子里,靠榆钱度日的老百姓可真不少。
榆钱还能怎么吃?高秀敏列举了很多种方法,比如撒上玉米面或者高粱面蒸榆钱饭就是其中一种。粮少的人家,面也搁得少,将将够把榆钱裹在一起,用腌咸菜的腌汤拌一拌,就是果腹的食物。烙饼子当然也很好,小小一块猪油润过锅,玉米面混杂着榆钱调好的面糊铺上去,刺啦一声,冒出一股子清香,孩子们趴在锅台上抽着鼻子闻,馋得口水滴答。
时至今日,榆钱也如苦菜一般,成了老百姓餐桌上的“风味儿”饭,榆钱在烹饪时也因为多了油盐酱醋而变得美味起来。
市民张广北就很喜欢自家楼下餐厅里每年春天的特色美食“榆钱粥”。将葱花或蒜苗炒熟后加水烧开,用大米或小米煮粥,米将熟时放入洗净的榆钱,再佐以胡椒粉、鸡精调味,吃起来滑润喷香,味美无穷,跟小时候吃的榆钱粥浑然不似一种东西。
“杯盘饧粥春风冷,池馆榆钱夜雨新。”怀念一碗榆钱粥,便似怀念一段旧时光。
香 椿
“一刀春韭胜珍馐,最美不过香椿头。”
春天的韭菜味道鲜美,香椿与其齐名,自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但香椿这种“鲜”却是要凭缘分的。
今年29岁的刘爽告诉记者,她最喜欢的野菜就是香椿,炸香椿、炒香椿、香椿鸡蛋、香椿豆腐,可谓是百吃不腻。
刘爽曾在南方求学,南方的香椿成熟的季节较之北方要早一些,暮春三月就能食鲜,北方的香椿则要等到农历四月左右才能成熟。
过去人爱吃香椿,大约也是因为秋冬季节少鲜菜的缘故,加之其维生素含量较高,老百姓视其为“补品”。如今人们吃香椿,大多吃的是风味。香椿的味道较为独特,很难形容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口感,也有人接受不了这种“恩赐”,觉得香椿真的是“除非果腹,否则毫无意义”的存在。
家住乌达区民达社区的曹煜曾经就是这样认为的。他家楼下有一棵香椿树,每年此时节,便是萌生嫩芽的时候。爷爷在世时,总要搬着梯子去摘香椿,回来裹上面炸成小面鱼给大家吃。别人吃得香喷喷,他却觉得“无福消受”。每每此时,爷爷就会笑他没口福,一遍一遍强调:“香椿升阳,暖胃通肾,是祛风利湿的好药。”
如今,爷爷过世三年,香椿树的嫩芽一茬一茬地冒,却再也没有一个小老头搬着梯子去采摘。曹煜每每站在阳台上看到那棵树,心里都会涌起深深的思念。突然有一日,他看到餐厅的桌上有一盘炸好的香椿鱼儿,不由得伸手捏了一根尝了尝,竟然吃出了以前不曾察觉的风味来。父亲端着茶缸走进来说:“香椿升阳,暖胃通肾,是好药哩。”
时光仿佛被折叠,曹煜说,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,父亲做香椿鱼儿,或许也是在怀念他的父亲。
大自然总是无条件地爱护着人类,野菜就是其中最好的馈赠。
乌海的春天很短暂,但乌海人食鲜的情结却深远。吃的是风味野菜,念的是岁月恒远。年复一年里,荣枯轮转中,生命便如野菜般,一茬冒一茬,春风吹又生。
本报记者 韩建慧/文 齐艳芳/图
[手机扫一扫]